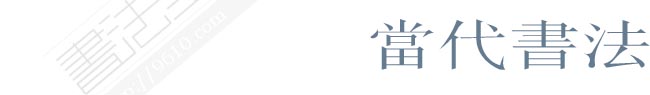立春已至,寒冷依舊。享譽(yù)海內(nèi)外的國(guó)學(xué)大師饒宗頤先生于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,享年101歲。現(xiàn)當(dāng)代國(guó)學(xué)家先后與錢鍾書、季羨林并稱為“南饒北錢”和“南饒北季”。

▲ 饒宗頤(1917.8.9 - 2018.2.6)
一代通儒
饒宗頤出生于1917年8月9日,字伯濂、伯子,號(hào)選堂,又號(hào)固庵,廣東潮州人。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著名的歷史學(xué)家、考古學(xué)家、文學(xué)家、經(jīng)學(xué)家、教育家和書畫家。
他出身書香名門,自學(xué)而成一代宗師。其茹古涵今之學(xué),上及夏商,下至明清,經(jīng)史子集,詩(shī)詞歌賦,書畫金石,無(wú)一不精;其貫通中西之學(xué),則甲骨敦煌,梵文巴利,希臘楔形,楚漢簡(jiǎn)帛無(wú)一不曉。人謂“業(yè)精六學(xué),才備九能,已臻化境”。錢鐘書說(shuō)他是曠世奇才,季羨林說(shuō)他是心目中的大師,金庸說(shuō)有了他,“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”,法國(guó)漢學(xué)家說(shuō)他是全歐洲漢學(xué)界的老師,當(dāng)代最偉大的漢學(xué)家,一代通儒。
饒宗頤在十四個(gè)門類的每一個(gè)領(lǐng)域的研究都有獨(dú)到之處。錢仲聯(lián)評(píng)價(jià)饒宗頤說(shuō):
所考釋者,自卜辭、儒經(jīng)、碑版以迄敦煌寫本;所論者,自格物、奇字、古籍、史乘、方志、文論、詞學(xué)、箋注、版本,旁及篆刻、書法、繪畫、樂(lè)舞、琴藝、南詔語(yǔ)、蒙古語(yǔ)、波斯語(yǔ),沉沉夥頤,新解瀾翻,兼學(xué)術(shù)文、美文之長(zhǎng),通中華古學(xué)與四裔新學(xué)之郵,返視觀堂、寒柳以上諸家,譬如積薪,后來(lái)居上。九州百世以觀之,得不謂非東洲鴻儒也哉!(錢仲聯(lián)《固庵文錄序》)
這也是學(xué)界的公論。
家學(xué)淵源
民國(guó)六年(1917年)八月九日(農(nóng)歷丁巳年6月22日),饒宗頤出生于粵東古城潮州的一個(gè)名門望族。
潮州,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唐代大文豪韓愈曾被貶官于此,在此停留期間,興學(xué)課士,留下不少名篇。宋代便有了“海濱鄒魯”的美譽(yù)。宋代以來(lái),這里商賈如云,人文鼎盛。饒宗頤的祖上原居江西,后輾轉(zhuǎn)入粵,定居潮州。
饒宗頤的父親在家中排行第三,名寶璇,初字純鉤,后改字鍔,號(hào)鈍鹿。饒老先生早年畢業(yè)于上海法政學(xué)校,飽讀詩(shī)書,留意時(shí)勢(shì),參加過(guò)當(dāng)時(shí)名震一方的革命團(tuán)體——南社。饒家世代儒商,在潮州開(kāi)有數(shù)座錢莊,宗頤出生時(shí),人稱潮州首富。饒老先生喜買書、藏書,將自己的藏書樓叫做“天嘯樓”,有書達(dá)十萬(wàn)卷。又工于詩(shī)文,精于考據(jù),于鄉(xiāng)邦文獻(xiàn)尤為留心,著有《佛國(guó)記疏證》、《潮州西湖山志》等書,還當(dāng)過(guò)《粵南報(bào)》的主筆。
饒宗頤的母親蔡老夫人則是名門閨秀,祖父蔡一桂在清同治年間曾任資政大夫,父親蔡子淵曾任戶部主事。只是蔡老夫人在宗頤兩歲時(shí)便去世了,母親清秀的模樣在宗頤的心里久久無(wú)法淡去,卻又無(wú)法清晰起來(lái)。
在父親的影響下,宗頤自幼便泡在天嘯樓的藏書里。“那么多書,我整天看,就像孩子在玩。我很早就能寫詩(shī)填詞,中國(guó)歷史從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,先后順序不會(huì)搞亂。”從《史記》到佛典,從老莊到還珠樓主,幼年的他無(wú)書不讀。有一次因?yàn)榘V迷于武俠小說(shuō),甚至寫了一部《后封神榜》。
饒老先生很早便著意培養(yǎng)自己這位長(zhǎng)子。宗頤六歲那年,便開(kāi)始練習(xí)國(guó)畫,后師從畫家楊栻?qū)W習(xí)繪畫山水、花鳥及宋人行草、名家法貼。宗頤酷愛(ài)任伯年的作品,曾將老師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臨摹殆遍,為其日后的書畫創(chuàng)作打下了堅(jiān)實(shí)的根基。宗頤的伯父既是畫家,又是收藏家,收藏的拓本、古錢頗多精品,為數(shù)達(dá)千種,他也時(shí)常把玩。

▲ 饒氏家族二十年代大合照,前排左五為饒宗頤。圖/香港大學(xué)饒宗頤學(xué)術(shù)館
此時(shí),宗頤的不少初中同學(xué)正在新式小學(xué)里從“手口足”開(kāi)始學(xué)習(xí)漢字,他們中的絕大多數(shù)將循著小學(xué)、初中、高中的新式學(xué)校建制前行。民國(guó)十九年(1930年),宗頤以優(yōu)異的成績(jī)考進(jìn)省立金山中學(xué)初中部,他發(fā)現(xiàn)老師講授的過(guò)于淺顯,讀了一年便覺(jué)得在學(xué)校實(shí)在有些浪費(fèi)光陰,徑直回家自學(xué)。相比之下,宗頤的心目中時(shí)時(shí)呈現(xiàn)的是家中的萬(wàn)卷藏書。
坐擁書城的饒宗頤,沒(méi)有辜負(fù)這得天獨(dú)厚的條件。跟一般孩童不同,他最喜歡的不是玩耍,而是學(xué)習(xí)。八十年過(guò)去了,饒宗頤對(duì)兒時(shí)的往事還歷歷在目:“我不大玩,是內(nèi)向的。六七歲就有這個(gè)drive,就有這個(gè)自動(dòng)(讀書學(xué)習(xí))的傾向,很奇怪。”才十歲左右他就跟著父親觀摩,幫助抄錄《佛國(guó)記》;父親寫《漢儒學(xué)案》、《新儒學(xué)案》等書,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,時(shí)常充當(dāng)幫手。
饒老先生家中常常高朋滿座,經(jīng)常一起論學(xué)唱和的多為潮州當(dāng)?shù)赜忻脑?shī)人柯季鶚、戴貞素等,畫家王顯詔、楊栻等,包括后來(lái)以詞學(xué)成家的中山大學(xué)教授詹安泰。此時(shí),宗頤往往隨侍在父親身邊,偶爾也參與酬唱。宗頤十六歲那年所作《優(yōu)曇花詩(shī)》,曾經(jīng)令舉座皆驚。詩(shī)云:
異域有奇卉,托茲園池旁。
夜來(lái)孤月明,吐蕊白如霜。
香氣生寒水,吐影含虛光。
如何一夕凋,殂謝滋可傷。
豈伊冰玉質(zhì),無(wú)意狎群芳。
遂爾離塵垢,冥然迫大蒼。
大蒼安何窮,天道渺無(wú)極。
哀榮理則常,幻化終難測(cè)。
千載未足珍,轉(zhuǎn)瞬詎為迫。
達(dá)人解其會(huì),葆此恒安息。
濁醪且自陶,聊以永今夕。
此詩(shī)一出,即被饒老先生的老師推薦給中山大學(xué)《文學(xué)雜志》發(fā)表,不少詩(shī)壇名宿都很驚詫,何以十六歲的少年能像陶淵明一般超脫,紛紛以詩(shī)唱和。當(dāng)時(shí)的中山大學(xué)中文系系主任古直驚為天人,許以“陸機(jī)二十作文賦,更兄弟閉門讀書十年,名滿中朝,君其勉之矣”,認(rèn)為假以時(shí)日,宗頤必能像陸機(jī)一樣文章冠世、名滿天下。古直早年投身革命,詩(shī)文冠蓋一時(shí),尤精于漢魏文學(xué),他對(duì)古代詩(shī)文的箋注體例精審、搜羅弘博,至今還被學(xué)界視為經(jīng)典。
正當(dāng)宗頤在父輩的薰陶下,讀書種子的氣象日益蔥蘢之時(shí),饒老先生卻因編纂《潮州藝文志》而心力交瘁,在宗頤十七歲那年便匆匆地離開(kāi)了人世。
彌留之際,饒老先生念茲在茲的是《潮州藝文志》尚未終篇。在約請(qǐng)父執(zhí)輩協(xié)助整理父親的詩(shī)文遺稿的同時(shí),宗頤決定獨(dú)自續(xù)寫《潮州藝文志》,并于一年后終于殺青。此書網(wǎng)羅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獻(xiàn),至今依然是潮學(xué)研究的必讀書,宗頤為之撰寫了精到的提要,奠定了其潮學(xué)創(chuàng)始人的地位。當(dāng)時(shí)的重要學(xué)術(shù)期刊《嶺南學(xué)報(bào)》將其全文連載。
那一年,饒宗頤十八歲。

▲ 天嘯樓
福地香港
1938年,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舉薦下,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(xué)研究員。當(dāng)時(shí)廣州已為日軍占領(lǐng),中山大學(xué)被迫遷往云南澄江。饒宗頤決心繞道香港前往云南,不料途中染上瘧疾,滯留香港。
饒宗頤后來(lái)常說(shuō)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緣分,因?yàn)槟鞘撬簧形ㄒ坏囊粓?chǎng)大病,他的命運(yùn)從此發(fā)生轉(zhuǎn)折。

▲ 香港大學(xué)饒宗頤學(xué)術(shù)館
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,曾擔(dān)任商務(wù)印書館總經(jīng)理,他發(fā)明了一套四角號(hào)碼,用來(lái)查甲骨經(jīng)文,后又想在此基礎(chǔ)上編一本八角號(hào)碼的《中山大辭典》,年輕有為的饒宗頤成了他的助手,幫助做一些圖書記錄工作,這也使饒宗頤第一次接觸到許多經(jīng)文的甲骨書,從此開(kāi)始對(duì)古文字產(chǎn)生興趣,并研讀大量的經(jīng)史子集。
葉恭綽是有名的書畫家與收藏家,曾擔(dān)任過(guò)北京大學(xué)國(guó)學(xué)館館長(zhǎng),建國(guó)后擔(dān)任過(guò)中央文史館副館長(zhǎng)。當(dāng)時(shí),葉恭綽正在編《全清詞鈔》,他請(qǐng)饒宗頤幫忙收集清詞,這段經(jīng)歷讓其對(duì)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為后來(lái)的詞研究打下基礎(chǔ)。
1949年,這一年也成為許多知識(shí)分子的轉(zhuǎn)折年。饒宗頤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,決定移居香港。從1952年開(kāi)始,饒宗頤在香港大學(xué)中文系任教16年,主講詩(shī)經(jīng)、楚辭、詩(shī)賦等,在英國(guó)人的統(tǒng)治之下,中國(guó)的學(xué)者沒(méi)有地位,直到離開(kāi)港大,他仍然只是講師,沒(méi)有評(píng)上教授。

▲ 饒宗頤 篆書
按他的話說(shuō),“因?yàn)橹袊?guó)人沒(méi)有權(quán)利講話,英國(guó)人要怎么樣就怎么樣。”好在他對(duì)身外浮名并不看重,在學(xué)術(shù)的天地里,自得其樂(lè)。這一時(shí)期,他對(duì)敦煌學(xué)、甲骨學(xué)用力最勤。
與大陸學(xué)者相比,身處香港的他,不僅沒(méi)有因?yàn)楦鞣N戰(zhàn)亂和政治運(yùn)動(dòng)中斷學(xué)術(shù)研究,甚至還可以接觸到海外的漢學(xué)研究。
1954年夏天,饒宗頤到東京大學(xué)講授甲骨文,同時(shí)到京都大學(xué)人文科學(xué)研究所研究甲骨文,在那里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。京都大學(xué)有數(shù)千片來(lái)自中國(guó)的甲骨文,但當(dāng)時(shí)日本學(xué)者并沒(méi)有引起重視,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(lǐng)下開(kāi)展研究,后來(lái)撰寫了《日本所見(jiàn)甲骨錄》,這在日本可謂開(kāi)風(fēng)氣之先。

▲ 饒宗頤 繪畫
此后,他又在法國(guó)、意大利等地,陸續(xù)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,一一加以研究。1959年,饒宗頤終于出版巨著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,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,將占卜的大事融會(huì)貫通,全面地展現(xiàn)了殷代歷史的面貌。
此書一經(jīng)出版,共有13個(gè)國(guó)家和地區(qū)發(fā)表評(píng)論,并加以推介,在中外學(xué)術(shù)界影響巨大。因?yàn)檫@部著作的發(fā)表,1962年法國(guó)法蘭西漢學(xué)院將“儒蓮漢學(xué)獎(jiǎng)”頒給了饒宗頤,這個(gè)獎(jiǎng)項(xiàng)被譽(yù)為“西方漢學(xué)的諾貝爾獎(jiǎng)”。
因研究領(lǐng)域的相似性,又有人將其與季羨林并稱“南饒北季”,與錢鐘書并稱“南饒北錢”。

▲國(guó)務(wù)院總理李克強(qiáng)2015年4月在北京會(huì)見(jiàn)饒宗頤。
多學(xué)并駕
饒宗頤的研究幾乎涵蓋國(guó)學(xué)的所有領(lǐng)域,根據(jù)他自己的歸納,其著述可分為:敦煌學(xué)、甲骨學(xué)、詩(shī)詞、史學(xué)、目錄學(xué)、楚辭學(xué)、考古學(xué)(含金石學(xué))、書畫等八大門類。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,他曾幽默地說(shuō),“我是一個(gè)無(wú)家可歸的游子”。
2009年《饒宗頤二十世紀(jì)學(xué)術(shù)文集》在大陸出版,共計(jì)十四卷二十冊(cè),超過(guò)一千二百萬(wàn)字,包含專著八十余種,論文一千多篇。學(xué)者稱其“業(yè)精六學(xué)、才備九能”,他則以“天地大觀入吾眼,文章浩氣起太初”這樣氣勢(shì)磅礴的對(duì)聯(lián),來(lái)表現(xiàn)其開(kāi)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。

▲ 饒宗頤 編著《全明詞》
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,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(xiàn),壯年由中國(guó)史擴(kuò)大到印度、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,晚年則致力于中國(guó)精神史的探求。季羨林曾評(píng)價(jià)他最善于發(fā)現(xiàn)問(wèn)題,絕不固步自封,隨時(shí)準(zhǔn)備接受新的東西,饒宗頤則說(shuō)季老懂我。
王國(guó)維曾把“新發(fā)見(jiàn)(現(xiàn))”歸納為五類:一、殷虛甲骨;二、漢晉木簡(jiǎn);三、敦煌寫經(jīng);四、內(nèi)閣檔案;五、外族文字。陳寅恪則說(shuō),“一時(shí)代之學(xué)術(shù),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(wèn)題”。而饒宗頤對(duì)新材料、新證據(jù)的重視和掌握,讓人吃驚。
季羨林在《饒宗頤史學(xué)論著選》序言中寫道,“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,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,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。他對(duì)國(guó)內(nèi)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,簡(jiǎn)直遠(yuǎn)達(dá)令人吃驚的程度。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游,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而是時(shí)時(shí)注意對(duì)自己的學(xué)術(shù)探討有用的東西。地下發(fā)掘出來(lái)的死東西,到了饒先生筆下,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。”
饒宗頤對(duì)國(guó)外的考古發(fā)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靈通,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,指揮若定,研究視野,無(wú)限開(kāi)闊。國(guó)內(nèi)一些偏遠(yuǎn)地區(qū)的學(xué)術(shù)刊物,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略,而他則無(wú)不注意。

▲ 饒宗頤和季羨林
事實(shí)上,人們將饒宗頤與季羨林并稱不無(wú)道理,他們兩人皆通曉多國(guó)語(yǔ)言,研究領(lǐng)域皆極為廣泛,在梵文、吐火羅文、敦煌學(xué)、佛學(xué)等領(lǐng)域有交叉研究,雖然見(jiàn)面機(jī)會(huì)不多,但兩人惺惺相惜,互相評(píng)價(jià)甚高。
有人說(shuō),饒宗頤鉆研的學(xué)問(wèn),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艱深的語(yǔ)言寫就的。他在40多歲學(xué)習(xí)梵文,60歲以后,學(xué)同樣有“天書”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,這些都是為了能直接讀懂最原始的經(jīng)典。
同時(shí),他與法國(guó)漢學(xué)研究者的交往加深,得以閱讀法國(guó)的大量敦煌古籍,想到當(dāng)時(shí)中國(guó)的敦煌學(xué)已經(jīng)落后于外國(guó),他暗下決心,一定要好好研究,為國(guó)人爭(zhēng)一口氣。不久他和法國(guó)漢學(xué)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《敦煌曲》,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,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(wèn)題。

▲ 饒宗頤在《敦煌白畫》中提到的二女神像
1978年前后他又獨(dú)立出版《敦煌白畫》一書,研究敦煌畫的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畫和絹花上,而《敦煌白畫》一書專門研究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,填補(bǔ)了敦煌學(xué)研究的一項(xiàng)空白。這兩部著作的問(wèn)世,也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(xué)研究領(lǐng)域的重要地位。
不管是甲骨文、梵文,還是敦煌學(xué)研究,饒宗頤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證據(jù),他的習(xí)慣是每一個(gè)問(wèn)題都要窮追到底,去學(xué)習(xí)不同的語(yǔ)言文字,也正是為了追根溯源。在他看來(lái),“這個(gè)過(guò)程是很有意思的,令我欲罷不能。我的求知欲太強(qiáng)了,這個(gè)求知欲吞沒(méi)了我自己。”
清華大學(xué)出土文獻(xiàn)研究與保護(hù)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,曾近距離追隨饒宗頤17年,讓她最難忘的是饒宗頤永遠(yuǎn)對(duì)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顆童真的好奇心,“正因?yàn)槊刻煊辛诉@一顆好奇心,才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”。

▲ 饒宗頤書法
饒宗頤經(jīng)常說(shuō),“我來(lái)不及看書,來(lái)不及煩惱”。他風(fēng)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識(shí)海洋里的“兩棲游物”,“我一天的生活,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,到了下午說(shuō)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,尋找著另外一個(gè)世界,另外一個(gè)天地。越是沒(méi)有人去過(guò)的地方,沒(méi)有人涉足的地方,我越是想探秘。”
沈建華介紹,饒先生的寫作通常是同時(shí)寫幾篇文章,并駕齊驅(qū),比如說(shuō)上午寫甲骨文,到了下午也許寫敦煌,到了晚上又是看簡(jiǎn)帛,遇到問(wèn)題就放一下,等到把這個(gè)問(wèn)題想通了,再繼續(xù)寫。“
有的文章幾天寫完,但是有的文章積累了三十年,像《漢字符號(hào)》這本薄薄的小書,他積累了三十年,一點(diǎn)一點(diǎn)寫。”所以,在她看來(lái),雖然饒先生的文集已經(jīng)出版,但是還有一些舊稿沒(méi)有發(fā)掘整理出來(lái)。
琴詩(shī)書畫
不少人將饒宗頤與王國(guó)維、陳寅恪相比,認(rèn)為他們?cè)谥螌W(xué)上既博且深,在許多領(lǐng)域開(kāi)風(fēng)氣之先,但王、陳二人皆沒(méi)有饒宗頤在藝術(shù)上的成就。
饒宗頤精通古琴,善于詩(shī)賦,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、自成一家。隨年歲日長(zhǎng),他的書畫作品越來(lái)越精到,已經(jīng)呈現(xiàn)出一種與前人全然不同的風(fēng)貌。2003年饒宗頤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,在香港大學(xué)建成饒宗頤學(xué)術(shù)館,這里掛滿了他的各類書法和繪畫作品。

▲ 饒宗頤山水
有人評(píng)價(jià),經(jīng)過(guò)半個(gè)多世紀(jì)的磨煉,師古人,師造化,得心源,他在技法上已經(jīng)從心所欲不逾矩,而他的性情與人生觀,也圓通無(wú)礙地融在畫中,使其畫作成為了傳說(shuō)中極其罕見(jiàn)的學(xué)者畫。因?yàn)槭煜ぜ坠菍W(xué)、敦煌學(xué),在他的書法之中又融入了許多古文字筆法。
饒宗頤平生最欽佩莊子的“參萬(wàn)歲而一成純”,這句話出于莊子的齊物論,齊物論的主要思想是將多與少、一萬(wàn)年和一瞬間,都看成同一回事,把一萬(wàn)年的精華提煉為純度很高的一瞬間。
饒宗頤在書畫創(chuàng)作上也運(yùn)用了很多齊物論思想,比如說(shuō)在一般人看來(lái),臨摹畫和創(chuàng)作畫是兩碼事情,但是從齊物論思想來(lái)說(shuō),他認(rèn)為,臨摹本身就是一種創(chuàng)作。他在臨摹過(guò)程中,也有自己的構(gòu)型、用筆,每一筆是他自己創(chuàng)作出來(lái)的。
他有一套自己的“饒功”,是一種瑜伽,一種打坐方法,有空就會(huì)在家練習(xí)。他說(shuō),每個(gè)人都有自己的天地,當(dāng)我閉眼的時(shí)候,我就讓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,可以想到幾萬(wàn)年、幾千里之外,此時(shí)我同天地融為一體,我已敲開(kāi)了莊子的門。
可能正是因?yàn)閷?duì)老莊和佛學(xué)的參悟,讓他對(duì)生死有超越性理解,也是他長(zhǎng)壽的秘訣。曾有人問(wèn)及他對(duì)王國(guó)維的評(píng)價(jià),他說(shuō)王國(guó)維是一位了不起的學(xué)問(wèn)家,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脫,這對(duì)他做學(xué)問(wèn)乃至詞學(xué)創(chuàng)造上的成就,也有一定限制。

▲ 饒宗頤揮毫
“一個(gè)人在世上,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,這是十分要緊的。”他認(rèn)為,陶淵明比王國(guó)維要明白得多,陶淵明生前就為自己寫下了“死去何所道,托體同山阿”的挽歌,由人生聯(lián)系到山川大地,已有所超越。王國(guó)維學(xué)康德,對(duì)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,所以他講境界,講到有我、無(wú)我問(wèn)題,雖已進(jìn)入到哲學(xué)范圍,但無(wú)法再提高一步。王國(guó)維如果能夠在自己所做學(xué)問(wèn)中,再加入釋藏及道藏,也許能較為正確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。
他常對(duì)人言,做學(xué)問(wèn)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,要有平常心態(tài),要“守株待兔”。不能急功近利。“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,而我就靠在樹底下,當(dāng)有兔子過(guò)來(lái)的時(shí)候,我就猛然撲上去,我這一輩子也不過(guò)就抓住幾只兔子而已。”
國(guó)之耆宿
饒宗頤先生是第一位講述巴黎、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學(xué)者,也是第一個(gè)系統(tǒng)研究殷代貞卜人物。1959年,他出版巨著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,以占卜人物為綱,將占卜的大事融會(huì)貫通,全面地展現(xiàn)了殷代歷史的面貌。
1962年,法蘭西漢學(xué)院將“儒蓮漢學(xué)獎(jiǎng)”頒給了饒宗頤。這個(gè)獎(jiǎng)項(xiàng)被譽(yù)為“西方漢學(xué)的諾貝爾獎(jiǎng)”。由此,饒宗頤與羅振玉、王國(guó)維、郭沫若、董作賓并稱為“甲骨五堂”。
七十年代,饒宗頤首次將敦煌寫本《文心雕龍》公之于世,成為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的第一人。他和法國(guó)漢學(xué)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《敦煌曲》,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,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(wèn)題。
此后,他又獨(dú)立出版《敦煌白畫》一書,專研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,填補(bǔ)了敦煌學(xué)研究的一項(xiàng)空白。這兩部著作的問(wèn)世,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(xué)研究領(lǐng)域的重要地位。
饒宗頤先生的研究領(lǐng)域,囊括了上古史、甲骨學(xué)、簡(jiǎn)帛學(xué)、經(jīng)學(xué)、禮樂(lè)學(xué)、宗教學(xué)等十三個(gè)門類,他出版著作六十余部,著述3000萬(wàn)言,僅《20世紀(jì)饒宗頤學(xué)術(shù)文集》浩浩十二卷,就達(dá)1000多萬(wàn)字。
他通曉英語(yǔ)、法語(yǔ)、日語(yǔ)、德語(yǔ)、印度語(yǔ)、伊拉克語(yǔ)等六國(guó)語(yǔ)言文字。其中梵文、古巴比倫楔形文字,在其本國(guó)亦少有人精通,而饒宗頤先生以中國(guó)人
卻能通乎異國(guó)“天書”。
饒宗頤精通古琴,還是撰寫宋、元琴史的首位學(xué)者,他善于詩(shī)賦,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、自成一家。2003年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,在香港大學(xué)建成饒宗頤學(xué)術(shù)館。
饒公佛緣
饒宗頤先生幼年即對(duì)佛教有很深的體驗(yàn),他曾在《宗頤名說(shuō)》一文中說(shuō),“自童稚之年攻治經(jīng)史,獨(dú)好釋氏書,四十年來(lái)幾無(wú)日不與三藏結(jié)緣。”他的書架上插滿了中文、日文版的《大藏經(jīng)》,以及泰國(guó)的《巴利文藏》。
民國(guó)初年,韓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寧年間的瓷器蓮花佛像,這些佛像不僅年代久遠(yuǎn),而且上面有窯工姓名,可以說(shuō)是很珍貴的,他的父親和伯父各買了兩尊。幼年的饒宗頤先生也非常喜歡這些佛像,他以后對(duì)這些佛像加以研究,發(fā)表了一篇有關(guān)陶瓷史的文章,引起了日本人的驚奇。
饒宗頤先生一次在日本旅游時(shí),偶然發(fā)現(xiàn)日本古代有一高僧也叫“宗頤”。他與人打趣地說(shuō):“若人真能轉(zhuǎn)世的話,我生前可能是位高僧。”
1981年秋,他游太原、大同等地,在華嚴(yán)寺旅游時(shí),饒宗頤教授無(wú)意中又發(fā)現(xiàn)有一經(jīng)書的寫序人的名字也叫“宗頤’,與自己名字相同,此人是北宋高僧釋宗頤。他看后,甚有感觸,即隨口賦詩(shī)一首:
竊喜同名得異僧,秋風(fēng)正馬事晨征。
華嚴(yán)寺前掛飄去,豈是生前此誦經(jīng)?
他于是制印一枚:“十方真定是前身”。
饒先生也看了不少佛書,對(duì)佛教深有研究,他在法國(guó)巴黎時(shí),曾展讀北魏皇興《金光明經(jīng)寫卷》,并曾著文論之。
他在生活中也非常想望一個(gè)清凈的世界,他曾對(duì)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胡曉明先生說(shuō):“有過(guò)一段時(shí)間真想剃度入山為憎。”
他還手書《心經(jīng)》,并曾“暮雨疏鐘憶六朝”,向往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樓臺(tái)煙雨中”。
饒先生十幾歲時(shí)就開(kāi)始學(xué)習(xí)打坐,而且每天堅(jiān)持,但是他畢竟沒(méi)有去過(guò)青燈古廟的生活,因?yàn)樗X(jué)得真正的道場(chǎng)并非僅僅在廟宇里,所謂心中有佛,處處是佛。
六十年代,饒先生在印度以40多歲的年紀(jì)開(kāi)始學(xué)梵文,至今他還能朗朗上口。在國(guó)外的3年中,他還向印度學(xué)者學(xué)習(xí)梨俱吠陀,足跡遍及印度南北;以后又游歷緬甸、錫蘭、泰國(guó)、柬埔寨等地,遂有了精深的佛學(xué)修養(yǎng),著有《佛國(guó)詩(shī)集》。
他說(shuō),印度人念經(jīng)有他的抑揚(yáng)頓挫,有些是念《圣解之歌》,還有早期的《梨俱吠陀》,他們都是唱的。其實(shí)中國(guó)古代的文學(xué)作品如詩(shī)詞歌賦等,大多也是可以唱的。我曾聽(tīng)已故上海佛教協(xié)會(huì)副會(huì)長(zhǎng)蘇淵雷教授唱古詩(shī),真的是很美妙。
饒先生雖然沒(méi)有出家,但他對(duì)佛學(xué)的悟性極高,因此北大季羨林教授稱贊他時(shí)說(shuō):“饒宗頤先生是能預(yù)流的。”
所謂預(yù)流果者,來(lái)源于南傳佛教,意思是指修行欲達(dá)最后之阿羅漢果,須自預(yù)流入,得預(yù)流果,即已除塵世煩惱而出俗人圣者也,也是得大道者。可見(jiàn)季羨林先生對(duì)他的評(píng)價(jià)之高了。
佛學(xué)成果
饒宗頤先生的佛學(xué)研究主要體現(xiàn)在他的《佛教淵源論》一輯中,收在饒宗頤先生“二十世紀(jì)學(xué)術(shù)文集”中,該輯有三篇文章,可以說(shuō)是代表了饒宗頤先生的主要佛學(xué)思想。
其中主要兩篇:一篇是《新州——六祖出生地及其傳法偈》(1989年),這是饒先生考察廣東省新興縣國(guó)恩寺及六祖故居后所做的研究,該文對(duì)六祖?zhèn)鞣ㄙ蕪姆鸬纼杉业浼姓业匠龅洹?/p>
另一篇是《惠能及〈六祖壇經(jīng)〉的一些問(wèn)題》,該文是饒宗頤先生在澳門舉行的《惠能與嶺南文化》國(guó)際學(xué)術(shù)研討會(huì)上的主旨發(fā)言,后收入《饒宗頤二十世紀(jì)學(xué)術(shù)文集》。他在文中說(shuō),“從我個(gè)人去新興的感受來(lái)說(shuō),惠能不應(yīng)是如《壇經(jīng)》等禪籍所描述的那樣目不識(shí)丁,國(guó)恩寺系惠能舍其故宅而建,面積很大。”因此,惠能很可能是有家世淵源的人。(《饒宗頤先生二十世紀(jì)學(xué)術(shù)文集》第五卷)
作為一個(gè)成就巨大的文化學(xué)者,饒宗頤先生對(duì)禪的理解也有獨(dú)到之處。他曾經(jīng)撰寫了《隋禪宗三祖塔磚記》(1988年)、《大顛禪師與心經(jīng)注》等文章,對(duì)于六祖惠能的研究,一直是饒先生比較感興趣的課題,他除了在一些專門文章中對(duì)此有研究外,在其他一些文章和談話中,也多次談了自己的看法,大致歸納起來(lái)有以下幾點(diǎn):
惠能禪與印度禪有很大的不同,中國(guó)的禪是可以活活潑潑地運(yùn)用于日常生活中,我們平時(shí)生活的一舉一動(dòng),都內(nèi)涵著一些禪理,而印度禪則不同,印度流行“禪窟”,是要人們?cè)谏钌焦哦蠢铮バ蘖?xí)苦行,有一種苦行僧的味道。所以饒先生說(shuō):“禪不光是要靜坐,而是要培養(yǎng)心中湛然一片光明海。”
饒宗頤教授認(rèn)為禪與藝術(shù)有密切的關(guān)系,在《八大山人禪畫索隱》一文中,他對(duì)禪與藝術(shù)的關(guān)系進(jìn)行了論述。《五燈會(huì)元》卷六《柘溪從實(shí)禪師》中有一段話說(shuō):
幽州柘溪從實(shí)禪師,僧問(wèn):“如何是道?”師曰:“個(gè)中無(wú)紫皂。”曰:“如何是禪?”師曰:“不與白云連。”師問(wèn):“僧作甚么來(lái)?”曰:“親近來(lái)。”師曰:“任你白云朝岳頂,爭(zhēng)奈青山不展眉?”
饒先生說(shuō),“'不與白云連。’讀起來(lái)很像謝靈運(yùn)的詩(shī)句。”他指出“禪家采用詩(shī)句型的語(yǔ)言來(lái)說(shuō)明深?yuàn)W的本體問(wèn)題,擺脫去名理上糾纏不清的邏輯性語(yǔ)言,單刀直入地用文學(xué)上'立片言之警策’的方法來(lái)啟發(fā)人們心理上的睿智。”“這種辦法可說(shuō)是'致知’上的一種藝術(shù)手段。”
所以,饒宗頤先生說(shuō),所謂“禪的世界,幾乎是詩(shī)的世界。”禪僧和詩(shī)幾乎是分不開(kāi)的,這在中國(guó)詩(shī)歌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。
在禪與畫方面,饒先生說(shuō),“畫家有時(shí)亦可運(yùn)用禪理去建立他的構(gòu)圖方案。”
他在《方以智之畫論》中,引用了方以智論畫的一段語(yǔ)錄,方以智說(shuō),畫“雖有六法,而寫意本無(wú)一法。妙處無(wú)他,不落有無(wú)而已。”
饒先生認(rèn)為:“此篇為極重要文字,指出畫之妙處,須不落入有無(wú)兩邊,匠筆、文筆二者皆饑。”此段話充滿了禪機(jī),所以饒先生把此稱為“禪機(jī)畫論”。
佛畫造詣
饒先生在美術(shù)實(shí)踐上也有很深造詣,尤其是他的白描佛像,有漢簡(jiǎn)筆法的遺韻,充滿了“古拙渾厚的意態(tài),真可以說(shuō)是白描的新發(fā)展。”(香港大學(xué)饒宗頤學(xué)術(shù)館藝術(shù)主任鄧偉雄:《從近代白描畫談到張大千、饒宗頤》)
中山大學(xué)教授姜伯勤對(duì)饒先生的白描畫有很詳盡的敘述,根據(jù)他的文章和《澄心選萃——饒宗頤的藝術(shù)》一書,可以為饒先生重要的佛像白描畫做一個(gè)簡(jiǎn)單的年表:
1979年,有朱色紙本立軸《諸天菩薩相》,這是對(duì)魏皇興五年《金光明經(jīng)·贊佛品》卷二的繪作。畫面上有一佛,二弟子,二脅侍菩薩。姜教授稱它“妙相莊嚴(yán),迦葉繪像有神采。”畫面以朱色行筆,因而別具古風(fēng)。畫上有題記。
1980年,水墨紙本16屏《十六應(yīng)真》。這是組畫作品,人物線描極富獨(dú)創(chuàng)性,將唐人白描畫技法中自簡(jiǎn)筆、顫筆、點(diǎn)構(gòu)、鉤斫諸技法,融為為一體,是畫家獨(dú)創(chuàng)性的典型。題記云:“海潮音一叫,說(shuō)道不要不要,頭面大時(shí)身不小。以唐人白描寫十六應(yīng)真。”
1981年,以朱筆寫《敦煌走獸人物》,卷末一幅為捧花菩薩,其畫題記云:“右伯希和三零五零號(hào)人物。以顫筆勾勒,縱意寫來(lái),毫不矜持,石窟白畫之上駟也。”
1985年,以白描寫紙本立軸《樹下觀音》圖,這是一幅六臂觀音圖,線條流利,觀音動(dòng)勢(shì)自然而莊嚴(yán),飄帶風(fēng)動(dòng),古樹繁密,形成疏密有致的對(duì)比效果,表現(xiàn)了佛教清涼世界的光明境界。
1993年,畫《布袋和尚》,這是他非常有特色一幅畫,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(zhǎng)鄭欣淼先生說(shuō)他此畫,用筆雖沿襲傳統(tǒng)畫法,神韻、意境卻不落尋常窠臼。他畫的和尚仰望秋月,若有所思。在畫作的右上方,饒先生還筆錄唐代詩(shī)僧寒山的一偈:“吾心似秋月,碧潭清皎潔;無(wú)物堪比論,教我如何說(shuō)?”實(shí)際上這也代表了饒先生自己的一種心境。
1994年,臨畫法國(guó)巴黎敦煌畫樣《供養(yǎng)人》,用線勁健,頗得唐人筆法。
1995年,有白描《觀音》、《無(wú)量壽佛》、《降魔菩薩》、《羅漢》等畫作。畫像有古拙之意,對(duì)袈裟的線描,更具匠心。
1996年,以白描手法寫水墨設(shè)色《觀音》、《敦煌大自在菩薩》等畫。
1998年,畫《云中觀音》、《敦煌觀音》和水墨《觀音》。
在饒先生的諸多畫作中,觀音畫是畫得比較多和有特色的,畫面莊嚴(yán)而透露出婀娜美麗,有時(shí)候,觀音頭頂金、藍(lán)寶冠,腳踏蓮花;有時(shí)候又華冠華發(fā),頗富裝飾意味。
在線條應(yīng)用上,有時(shí)用顫筆寫成彩云衣紋,用這種手法增添了天上人間的氣象;所謂戰(zhàn)筆,中國(guó)古代人物衣服褶紋畫法之一。此描法近似水紋波浪,故名。用中鋒下筆尤宜藏鋒,衣紋重疊似水紋而頓挫,疾如擺波。《萱和畫譜》“周文矩……善畫,行筆瘦硬戰(zhàn)掣,有煜(南唐李后主)書法。”
有時(shí)又用流暢而淡雅的線條,別有一番體現(xiàn)了當(dāng)代畫家對(duì)人體造型的素養(yǎng),看饒先生的白描畫,使人能從柔和莊嚴(yán)的畫境中,得到某種精神的感染。
看饒宗頤先生的觀音畫,心如蓮花般的清靜,看無(wú)量壽的畫像,使人產(chǎn)生尊重恭敬之心。
有人評(píng)論他的觀音畫是“流暢而富有畫家獨(dú)創(chuàng)性的淡雅的用線,有一種回旋的音樂(lè)美,使人頓悟'觀其音聲皆得解脫’的意境。這是畫家出入傳統(tǒng)而深悟新世紀(jì)當(dāng)代人審美情趣的佳作。”(姜伯勤《“不了可通神”:論藝術(shù)與生命的超越》)
而看饒先生的《敦煌大自在菩薩》,傳達(dá)出“轉(zhuǎn)苦以為樂(lè)”的大自在的境界。饒宗頤先生佛畫的成功,在于他深得唐人畫法,而且能推陳出新,使傳統(tǒng)和現(xiàn)代性融于一爐。
就中國(guó)藝術(shù)而言,禪的思想和意境對(duì)其影響是巨大的,饒先生說(shuō):“禪家之學(xué),影響及于藝事,自元以來(lái),已深入詩(shī)流畫伯之心坎。”
他的一首論畫詩(shī)云:“何當(dāng)?shù)卯嫳阃?shī),騷首無(wú)須更弄姿。惟有祖師彈指頃,神來(lái)筆筆華嚴(yán)時(shí)。”也將神來(lái)之筆,歸于佛心禪意。
饒先生自己的書畫充滿了深深的禪意,極其自然,于淡淡的幾筆勾勒中,透出一種清明之氣。著名的藝術(shù)評(píng)論家黃苗子說(shuō),以畫入禪或以禪入畫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自宋以來(lái)的畫家,也有畫與禪結(jié)合的好作品,如梁楷、石恪、牧溪、清初八大、石濤等,雖然他們的筆墨風(fēng)格不同,但都是通過(guò)悟禪修心得來(lái)的成果。
饒先生的畫落筆便高,也說(shuō)明他禪學(xué)修養(yǎng)很高。心中沒(méi)有執(zhí)著,下筆自然隨意,所謂隨意,是指筆隨心意走,他把禪宗的有、無(wú)、色、空概念,融化在丹青里面,表面上不落一個(gè)禪字,而畫面上透出絲絲禪意,他的一景一物,一草一花,一人一僧,看是隨手拈來(lái),無(wú)心無(wú)意,實(shí)是匠心所在,這就是饒先生畫作的特點(diǎn)。
從他的一首詩(shī)中,也可略見(jiàn)其端倪。詩(shī)云:“水影山谷盡斂光,靈薪神火散余香。拈來(lái)別有驚人句,無(wú)鼓無(wú)鐘作道場(chǎng)。”這就是他在書畫藝術(shù)上所追求的境界。

▲饒宗頤觀音畫
歸去來(lái)兮
一九八零年,饒宗頤回到離開(kāi)三十年的大陸,徜徉于神州秀美的山川。然而,在四處訪古的同時(shí),他尤為關(guān)切的是新中國(guó)的出土文物。針對(duì)在湖北發(fā)掘的秦簡(jiǎn)、編鐘,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請(qǐng)此次陪同者、中山大學(xué)曾憲通赴港合作研究,著成《云夢(mèng)秦簡(jiǎn)日書研究》和《隨縣曾侯乙墓鐘罄銘辭研究》二書,被學(xué)界譽(yù)為“研究秦簡(jiǎn)日書及振興中國(guó)鐘律學(xué)的奠基之作”。
這次中國(guó)文化之旅,是饒宗頤治學(xué)經(jīng)歷甚至是他一生的又一重大轉(zhuǎn)折,長(zhǎng)達(dá)三個(gè)月的實(shí)地考察,使他接觸到更為廣博的古代文物。饒宗頤還在北京拜見(jiàn)了已重病住院的顧頡剛,顧老先生雖已年近九旬,記憶力卻很好,見(jiàn)到饒宗頤說(shuō)他們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,一直還保存著饒宗頤早年為《古史辨》所寫的好幾篇文章。當(dāng)時(shí)饒宗頤動(dòng)情地說(shuō):“那是我小孩子時(shí)寫的東西,還請(qǐng)顧老多多指教。”饒宗頤回到香港數(shù)月后,便接到了顧頡剛?cè)ナ赖南ⅰ>蛯?duì)學(xué)術(shù)的好奇心和問(wèn)題意識(shí)而言,饒宗頤與顧頡剛有很多共通之處。
一九八二年,《選堂集林?史林》出版,被學(xué)界譽(yù)為繼錢鐘書《管錐篇》后的又一學(xué)術(shù)巨著,有人稱譽(yù)為“南北學(xué)林雙璧”,他造訪錢鐘書時(shí),錢以自己批校過(guò)的《管錐編》手稿相贈(zèng)。之后饒宗頤又先后推出《固庵文錄》、《甲骨文通檢》、《中印文化關(guān)系史論集——悉曇學(xué)緒論》、《詞學(xué)秘笈之一——李衛(wèi)公望江南》、《敦煌琵琶譜》、《近東開(kāi)辟史詩(shī)》、《敦煌琵琶譜論文集》、《〈老子想爾注〉校證》、《文轍——文學(xué)史論集》等書,耄耋之年依然筆耕不輟。
當(dāng)饒宗頤再回大陸時(shí),民國(guó)的學(xué)術(shù)前輩和同輩大多已凋零殆盡,季羨林已經(jīng)算是老輩學(xué)者的領(lǐng)袖。饒宗頤除了與季羨林在梵學(xué)、敦煌學(xué)方面頗有共通之處外,還十分贊賞季羨林樸實(shí)敦厚的學(xué)風(fēng)。季羨林則對(duì)饒宗頤推崇備至,盛贊饒:“近年來(lái),國(guó)內(nèi)出現(xiàn)各式各樣的大師,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。”
“國(guó)學(xué)”何以可能?
饒宗頤其實(shí)并不太認(rèn)可“國(guó)學(xué)”這一稱謂。相對(duì)而言,他更愿意使用“華學(xué)”或“漢學(xué)”這類的字眼。對(duì)于中國(guó)學(xué)術(shù)的前景,饒宗頤頗有信心,在他看來(lái),中國(guó)現(xiàn)在已有不少學(xué)術(shù)人才可以獨(dú)擋一面,不過(guò)他一直強(qiáng)調(diào)為學(xué)必先敦品。
提到饒宗頤,人們津津樂(lè)道的是其家學(xué)淵源。饒宗頤認(rèn)為:“以我的經(jīng)驗(yàn),家學(xué)是學(xué)問(wèn)的方便法門,因?yàn)樽鰧W(xué)問(wèn),‘開(kāi)竅’很重要,如果有家學(xué)的話,由長(zhǎng)輩引入門可以少走彎路。現(xiàn)在的家學(xué)已經(jīng)到了末路,我覺(jué)得有家學(xué)基礎(chǔ)的學(xué)生應(yīng)該被作為特殊人才來(lái)培養(yǎng)。”
回顧走過(guò)的路,饒宗頤感嘆:“我發(fā)現(xiàn)呢,最受用的,我到今天還受用的,就是我的文章的根底,文字的掌握。”他認(rèn)為,要做到古人講的“通”,首先文字就得通,要真正“懂得字”。雖然為此讓學(xué)童背誦古文有些無(wú)聊,但就自己的經(jīng)驗(yàn),饒宗頤覺(jué)得只有這樣文氣才能通,“你有這個(gè)底子呢,你看古人的東西,就能弄清,你自己就會(huì)做,模仿它的調(diào)子,等于你唱戲,(根據(jù))甚么調(diào)子,同一個(gè)道理。你也就覺(jué)得有趣味了”。
說(shuō)此話時(shí),饒宗頤或許想到了自己讀初一時(shí)的經(jīng)驗(yàn)。當(dāng)時(shí)有位叫王弘愿的老師,指導(dǎo)他學(xué)古文要從“韓文”入手。這對(duì)饒宗頤影響很大,至今他還很信服:“現(xiàn)在我還是要談作文應(yīng)從韓文入手,先立其大,先養(yǎng)足一腔子氣。”
中國(guó)古人尤其是清代學(xué)者治學(xué)講“讀書必先識(shí)字”,先讓孩童從王筠的《說(shuō)文蒙求》入手,再讀《說(shuō)文解字》,同時(shí)跟著老師念經(jīng)書,培育對(duì)文字的感覺(jué)。饒宗頤這一心得似乎還還少被人提及。
今天,國(guó)學(xué)教學(xué)研究機(jī)構(gòu)在大陸紛紛建立,可惜主持者并未能夠擺脫理工科式評(píng)估體制的束縛,國(guó)學(xué)的學(xué)科定位也面臨難產(chǎn),對(duì)于國(guó)學(xué)的認(rèn)識(shí)更多的是大而無(wú)當(dāng)。國(guó)學(xué)的舊事重提看重的更多的是“國(guó)”,面對(duì)深諳傳統(tǒng)學(xué)術(shù)的前輩凋零的格局,國(guó)學(xué)在制度層面似乎有些畫餅充饑。在新式學(xué)科的阻隔之下,在人文學(xué)科修習(xí)者就業(yè)形勢(shì)日益嚴(yán)峻之后,如何才能突破學(xué)科藩籬,如何才能在治生的同時(shí)安心學(xué)問(wèn),又如何補(bǔ)上對(duì)于古典的失憶性空白?
二零零三年,饒宗頤教授將個(gè)人積累的數(shù)萬(wàn)冊(cè)貴重藏書,包括非常珍貴的古籍善本,以及一百八十多件書畫作品,捐贈(zèng)給香港大學(xué),借以回饋香港。這些藏書絕大多數(shù)都有饒宗頤的批注,今后的研究者有幸,可以沿著閱讀史的思路對(duì)饒宗頤的學(xué)術(shù)源流進(jìn)行細(xì)密的剖析。很多漢學(xué)家,不分國(guó)界、種別,就像饒宗頤原來(lái)不斷前往法國(guó)遠(yuǎn)東學(xué)院、日本京都大學(xué)人文科學(xué)研究所一樣,時(shí)常來(lái)到饒宗頤學(xué)術(shù)館做研究,漢學(xué)的視線在往復(fù)中熠熠生輝。
饒宗頤以一人之力,為世人勾勒出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的整體輪廓,并將這一場(chǎng)景完美地展示給世界,然而他卻如此的謙和。儒家所說(shuō)的君子,庶幾近之吧?
作為不世出的文化奇跡,饒宗頤是不可復(fù)制的。我們能做的,或許是備好天才生長(zhǎng)的土壤,允許其孤獨(dú)的土壤,大師的誕生才不再是神話。
泰山其頹,哲人其萎。
饒宗頤先生千古!
本文轉(zhuǎn)自百度百科
长寿区| 姜堰市| 沁阳市| 赤壁市| 孝义市| 沂南县| 裕民县| 耿马| 福海县| 富民县| 银川市| 科技| 古交市| 固安县| 探索| 永胜县| 松潘县| 团风县| 乌兰浩特市| 轮台县| 彰武县| 广南县| 苏州市| 闻喜县| 镇原县| 张家界市| 汉沽区| 麦盖提县| 宝兴县| 德兴市| 滦平县| 福贡县| 南召县| 百色市| 平远县| 德保县| 布尔津县| 盐亭县| 尚志市| 凤冈县| 三明市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