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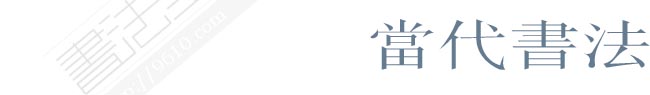

| 當(dāng)代書壇 | 書法組織 | 書法人物 | 香港 | 臺(tái)灣 | 韓國 | 日本 | 更多 |
我和書法篆刻
劉一聞
我對(duì)書畫藝術(shù)的愛好始于孩提時(shí)代。或許是多少有點(diǎn)“家庭熏陶”的緣故吧 ,那時(shí)的我,對(duì)大人們寫字畫畫的那種特有的神態(tài)就懷有一種神秘感。正是由于 這種神秘感的驅(qū)使,居然也模仿著大人們的樣子,煞有介事地“干”開了,從此 ,一發(fā)便不可收。說來也奇怪,當(dāng)時(shí)有多種興趣的我,到念中學(xué)時(shí),便先后把愛 好多年的航模、收音機(jī)、話劇表演和器樂、作曲等逐個(gè)地疏棄了。
想不到十年動(dòng)亂給了我充裕的時(shí)間,使我得以“正而八經(jīng)”地用了些功。隨 著年齡的增長,我從單純愛好,逐漸上升為有意識(shí)的“攻讀”。先后臨摹了為數(shù) 可觀的古代書法作品,其中有《褚遂良大字陰符經(jīng)》、《顏勤禮碑》、《懷素自 敘帖》、《禮器碑》、《居延汗簡》等,對(duì)于讀碑、讀帖,我也花去了大量的時(shí) 間。我覺得,作為藝術(shù)的練功,固然十分必要,但若一味地“練死功”,那將無 異于把藝術(shù)進(jìn)行“規(guī)范”后趕進(jìn)死胡同,因?yàn)樗囆g(shù)本身就是情感和思維的傳達(dá)呀 !因此,在具備了一定的“功力”之一,更重要的則是加強(qiáng)其他方面的修煉,以 不斷積累“悟性”。為此,我便把吟詩、看畫(包括名作題跋)、聽音樂也同樣 地作為“日課”,年復(fù)一年地持之于今。
在研習(xí)書法的同時(shí),我還系統(tǒng)地閱讀了有關(guān)篆刻的專著和史料,涉獵歷代名 作。尤其得天獨(dú)厚的是,舅父曾多次將先外祖王獻(xiàn)唐的部分遺著如《平樂亭侯印 考》、《五燈精舍印話》、《臨沂封泥考略》及手稿、日記和文革尚未被抄毀的 原始資料出示與我,使我飽覽其中,茅塞頓開。之后,我將部分家藏古印以分類 整理、歸納,請益于學(xué)術(shù)界前輩、獻(xiàn)公生前好友容庚、商承祚和方介堪諸先生, 收獲頗多。
一九七一年,我隨母親去青島省親,經(jīng)舅父介紹,結(jié)識(shí)了山東篆刻家蘇白教 師這是一位在我學(xué)習(xí)的轉(zhuǎn)折時(shí)期給我以莫大幫助、令我終生難忘的、使我至今回 想起來仍充滿了感情的清廉遜和的長者(盡管他病逝時(shí)年僅五十七歲)。尤其難 能可貴的是,當(dāng)時(shí)尚處在逆境中的蘇白老師,自一九七二年起直到他逝世前,一 直“函授”于我整整十二個(gè)年頭(其間授函達(dá)四百封之多!)。可以說,在篆刻 的園地里,我之所以能學(xué)步至今,都是和蘇白老師的諄諄教誨分不開的。
幾乎與此同時(shí),我參加現(xiàn)代字刻印探討,有幸求教于著名金石家方去疾。去 疾先生素以治學(xué)嚴(yán)謹(jǐn)、獎(jiǎng)掖后進(jìn)蜚聲藝壇。多年來,承先生不棄,我一直親聆教 導(dǎo)、蒙受點(diǎn)撥。在我汲取傳統(tǒng)養(yǎng)料的各個(gè)階段,是他把扶著我亦步亦趨。
藝術(shù),是人格化了的自然。一件藝術(shù)品的誕生,是多項(xiàng)基因互為作用的合成 ,書、畫、篆刻無不例外。當(dāng)然,有良師的躬親教誨,不能不說是創(chuàng)作的有利條 件,然而,欲使自己在創(chuàng)作中得到映現(xiàn)并使之異峰突起,歸根到底,還是“學(xué)識(shí) ”、“修養(yǎng)”的衍化。不然,心雖騖遠(yuǎn),而心手不一,腕下出現(xiàn)的終究是前人作 品的摹仿和翻刻。
回顧自己的學(xué)習(xí)過程,客觀上固然是由于家庭為我提供了一定的條件,但如
何在前輩們的發(fā)蒙和指點(diǎn)下,在把握繼承和貫通(實(shí)為“借鑒”和“自創(chuàng)”)的
關(guān)系中,多用心腦、多下工夫,我體會(huì)這是至關(guān)重要的。
聲明:本版圖片由于無法得到作者授權(quán),不作商業(yè)用途,如涉及侵權(quán),請速與本站聯(lián)系,我們立即刪除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