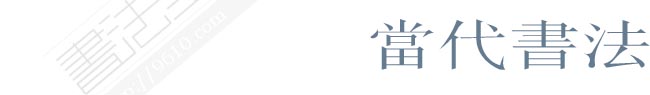

| ���ﺆ(ji��n)�� | ��Ʒ���p | 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 |
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
÷ī��(199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b��o)��)
�����ڹŴ���Փ���(du��)�ڡ���ɡ��͡���퍡��ď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S̎��Ҋ����ɮ�P��ٝ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�ϣ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֮����֮�߷��ɽB�ڹ��ˡ����@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Ξ鸱���ı��C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ѭ��s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Ψ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ߣ�Ψ�^��ɣ���Ҋ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ϣ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͡�Ψ�^���ą^(q��)�e����Ҫ�nj�(du��)�ڡ��Ρ���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J(r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�Щ�p�صIJ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@Ȼ�Ǵ��ڵģ��Ǿ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ġ���(j��ng)κ�x�ϳ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ġ���ɡ��c����⡱�f�����Ӱ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^��@���S��Դ��κ�x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Մ�L(f��ng)�⣬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dz���ҕ�L(f��ng)���c��퍵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Բſ��ܮ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Z���ǘӵ�ӛ���c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Ʒ���@һ�r(sh��)�ڵ��S����Փͬ�ӎ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퍵�ɫ�ʣ��@�Dz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ֱ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塢�Sɽ�ȵ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⡢����顰�W(xu��)��֮Ҫ���폊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K�Y���^ȫ��Щ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⡢�ǡ�Ѫ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ɕ�Ҳ�����@Ҋ���mȻ�K�Y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���Ҫ��λ��Ȼ�Dz��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^�ֲ��ɱ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Ʒ��ȱ�ل�(chu��ng)��Ʒ�|(zh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D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Ȼ��(x��)�Ԟ鳣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ڟo�M�Ă��y(t��ng)ģʽ�ĺ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ȥ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棬�����^�˂��y(t��ng)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w�\�ؑ{�ճ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Ю���(bi��o)�£���ȱ�ٸ���Ҳ���ö��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ӳ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X�Dʽ����ȻҲ�x���_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Ԫ���ΑB(t��i)���ڡ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X�Ŀ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Ѡ�B(t��i)��(d��ng)Ȼ�ǽy(t��ng)һ�����C�ġ���ʽ�c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y��ng)ԓ�ǡ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֮�⡱�ġ�ͨ��Ԫ֮�����ɡ��ھ��w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У����Ҷ���(sh��)�y������،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@һ�c(di��n)���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s�ֲ��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ȥ�w�J(r��n)�R���Ե��вݕ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y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ݕ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Č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ӵ����c���㡣���R���Ԇ����IJݕ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퍵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ȱ�٣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l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ژ�(g��u)��ҕ�X���g�^���У��O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赸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ʽ�Ĺ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⾳�c�ζ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_(d��)�Ƿdz�ֱ�ӵġ������@�Tˇ�g(sh��)�ڲݕ��w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ӵر��_(d��)�˵���־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ڲݕ��]���^���е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c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^�ˌ�(du��)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Բݕ��ɰl(f��)֮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Įa(ch��n)���(du��)�ڲݕ���ҕ�X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퍡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ȵȵİ����c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γ����R���Բݕ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ֱ�X�ԡ����䏈�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ه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Č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cԊ(sh��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x��˷�Ļ��X���g���f��ͨ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Ԓ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ڠI(y��ng)��(g��u)һ�N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Dͨ�^�@�N�����Ě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Ρ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Ҳ�_��(sh��)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@�N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Ʒ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ң����IJݕ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Ի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c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؟(z��)�θеĕ���һ�ӣ������ܼ��ء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˼���^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ǚ����ߑ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ؽ�(j��ng)�A�Σ�ÿλ���ҵ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õġ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۵ġ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gҲ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ġ��⡱���Ѕ^(q��)�e����ˣ�ǧ�˰ّB(t��i)�ġ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ǧ�˰ّB(t��i)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ǂ�(c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�ɡ��c����퍡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cī퍵�׃�����dz��挍(sh��)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˪�(d��)���r����ҕ�X�L(f��ng)��ֱ�X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��ʽ��(g��u)�ɵĹ�(ji��)��׃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c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^�л�ȡ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IJݕ���(sh��)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X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Ի��ij���PīȤ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ҕ��(du��)��Ȼ�c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^�졢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ЫCȡ�ݕ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ǡǡ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ڳɾ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p�صġ�Ҳ�S�@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Ȼ�Ć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(c��)����V�҂����ܷ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Ȼ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ďV����ȥ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Ҍ��nj�����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ζ�\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Ƕ�ô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ָ���ģ����˷��أ��ط��죬�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(d��ng)�ƺ��x���_���⎟�컯���е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@��һ�l��׃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(g��)픷��A�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ʽ�����ɞ齩����ģʽ���λ\һ�����ğ�ە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Ȼ��ȱ�١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֮�����̛]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֮�H��ֻ�Ъ�(d��)���R(sh��)Ҋ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Ӳſ��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҂��ѳ���ij�N�ݛ]֮�ȣ����^���ԣ���Щ���Ҹ��X���õĕ��ҾͿ�Ц���ˣ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Y�Y(ji��)�Ժ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(g��)�˶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һ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ġ���ˣ���Щ���R(sh��)�ڴ˲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lѪ·�ĕ���֮���FҲ�Ͳ��Զ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˷N���ҕ֮��
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f�Բ������˝M�⡣�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ʬF(xi��n)�ă�(y��u)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c��¶�IJ��㲢�B(t��i)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K�|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ġ������Iһ������ɕ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ȱ�١��ǡ��@һ�(xi��ng)Ҫ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ͬ���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ęM����^߀���c�v���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Ŀv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ʽ�ľ��l�ΑB(t��i)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ҽ^���ܔ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]�л�ȱ�ٹ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Ԯa(ch��n)���@�N�z�����@�Dz��ûش�ġ�
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ԕ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Ȼ��Xȡ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O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Ě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Z�R���o�ɘO�І�ʾ���á���Ʒȱ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н����õ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Լ��ɴ˶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?g��u)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©�ۣ����͉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㡣�^���p�@ƣܛ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ֵĄ�(d��ng)�B(t��i)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S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м��У�Ҳ�C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du��)��׃�õ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˼���@һ�Пo���з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δ��̽���У��R���ԕ����ܷ�����ҵľ��l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8K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Ƭ���ڟo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̘I(y��)��;�����漰�֙�(qu��n)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c��վ(li��n)ϵ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